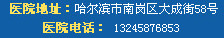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馮茜
原刊《漢學研究》第38卷第4期
摘要
關於中國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日本法史學家仁井田陞與滋賀秀三之間存在分歧。仁井田陞認為,在祭祀繼承人的選定上,?嫡系主義?與?行輩主義?兩大類型因時代不同而互有消長;滋賀秀三則主張,相應於財產上的諸子均分,秦漢以下的繼嗣承祀原則表現為?行輩主義?對?嫡系主義?的取代。區分?嫡系?還是?行輩?繼嗣的一大關鍵在於考察?嫡孫?的地位。體現宗法嫡系繼嗣原則的?嫡孫承重?服制,為反思上述爭議提供了重要視角。魏晉至唐代,?承重?大致保留了經典古禮?承宗廟、爵土之重?的制度意涵,?嫡孫承重?主要施行於封爵世襲之家。宋代臣僚無世爵,?嫡孫承重?失去社會基礎,熙寧八年(),行輩優先的承重順序正式從法律上得以確立。與此同時,政治制度不再對?嫡孫承重?向士庶普及構成制約。得益於士大夫對宗法理論的普遍化重釋及其禮儀實踐,元明清代禮法繼承《家禮》中的?嫡孫承重?,深刻影響了習俗中的承祀服喪。習俗的多元及考證禮學對禮制經驗之維的強調下,?嫡孫承重?禮制在清代仍是富於爭議的話題。經典、習俗與禮法的交互作用,使得秦漢以下的繼嗣承祀並非?行輩?對?嫡系?原則的簡單取代。展現其中的複雜性,有裨理解古人看待禮的不同方式。
關鍵詞:嫡孫承重嫡庶行輩繼嗣承祀
馮茜老師
一、前言
在中國古代,繼嗣相續是家庭繼承的重要方面。關於繼嗣原則的歷史變化,已故日本中國法史學界的兩位泰斗——仁井田陞與滋賀秀三之間存在很大分歧。仁井田陞認為,祭祀繼承人的選定,自古以來存在?嫡系主義?與?行輩主義?兩大類型,兩種類型的採用程度,因時代不同而有高低之別。[1]滋賀秀三則提出,隨著周代宗法封建制的解體,秦漢以下,包括承祀在內,私法領域的繼承原則已由嫡系繼承讓位於行輩繼承。嫡系繼承只在關涉封爵、世職等公法問題時才有意義。[2]就此問題,中文學界研究法制史與宗族史的學者,觀點多與滋賀秀三接近,但也存在類似爭議。[3]
學者指出,在周代宗法制下,祖父和長孫的關係變得非常密切,甚至超過了父子關係,?只有明確規定兒子死後必須由孫子繼承,才能防止『兄終弟及』現象的出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嫡長子繼承制的本質就是『立孫之制』。?[4]也就是說,考察承繼原則中的?嫡系?與?行輩?因素,其核心是對?嫡孫?地位的分析。淵源於《儀禮》喪服經傳中的?傳重?、?受重?,凝結為後世討論宗祧傳承的專門術語,而?嫡孫承重?則以服制形式反映了宗法制下的嫡系承祀原則,其歷史變化,為理解古代繼嗣問題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觀察視角。喪服禮制在歷史上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嫡孫承重?服亦莫能外。魏晉禮議與唐宋元明清禮典、律令中一直存在的?嫡孫承重?服,構成了對滋賀學說的一大挑戰。就此,滋賀秀三專門寫作了承重について一文加以解釋。滋賀秀三認為,明清時代的?承重?一詞,已喪失祭祀相續之意,轉訛為僅表服祖斬衰重服的喪服術語。魏晉以降,?承重?之?重?,已漸由喪禮中暫代神主之?重?,轉意為斬衰?重?服之?重?。[5]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滋賀秀三進一步闡述了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在經過戰國的激動期出現根本變化的秦漢以後的社會體制中,特別應當尊重嫡長一系的實質性條件一般來說已經不存在。?[6]進一步,滋賀認為,理解中國古代私法上的繼承,應將繼嗣、祭祀與承財三者一體看待,其背後則是父子分形同氣、兄弟平等的思想。[7]?嫡孫承重?的上述變化與秦漢以下財產繼承中的諸子均分,正是同一原理的不同面向。
《儀禮疏》書影,嘉慶張敦仁刻本
由?嫡孫承重?的視角切入,雖無法涵蓋繼承問題的各個方面,卻頗有助於對滋賀理論及繼嗣承祀原則作進一步反思。本文系統梳理?嫡孫承重?服制長時段的演變歷程,並立足時代情境解析影響服制變化的相關因素。在經典、禮法與習俗的交互作用下,?嫡孫承重?的變化呈現出了較複雜的歷史圖景。由此帶來的啟示是,喪服實踐及其關聯的繼嗣承祀,並不是被單一原則或單一觀念所決定,揭示其中的矛盾與衝突,有助加深對古代禮儀生活之理解。
二、從經典到成文法:魏晉至唐代?嫡孫承重?服制的身分問題
?嫡孫承重?意即在祖卒而無嫡子可繼承宗祧的情況下,由嫡孫上承祖重,為祖服斬衰,體現了周代大宗法制下的嫡嫡相承。經典所代表的理想周制,為後世禮法中的?嫡孫承重?提供了理念型。不過,喪服實踐中的?嫡孫承重?並未始終如一地貫徹其經典原意,而是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演進。漢代喪服無定制,?嫡孫承重?作為具有規範意義的制度存在,始於曹魏。嫡孫承重為祖之服,在喪服經中並無明文記載。喪服傳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8],《禮記》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9]基於傳記文字與宗法原理推斷,嫡孫承重為祖服斬,在經學上應無疑義。但在曹魏時期,圍繞?嫡孫承重?服斬在經義上是否成立,卻產生了較大爭議,如魏人成洽、劉寶就拒絕承認?嫡孫承重?為祖服斬的經學根據。劉寶議云:
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古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為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小記與傳但解經意耳。傳稱者此祖後,謂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己上厭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10]
劉寶提出,喪服小記?為祖後者為祖母三年?,意指?無後養人子以為孫?,並舉荀顗無子、養兄孫以為己孫作為例證。這只承認了以孫後祖中的一種情況,即無後而以旁支庶孫為後。事實上,祖之嫡孫上承祖重,無疑屬於經文所說?為祖後?者。劉寶又論?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古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無子而以旁支孫為祖後,為?間代取後?,若如劉寶論,此時祖孫關係同於父子,孫為祖服斬實即子為父服,將導致昭穆的混亂。顯然,劉寶窄化了經文?為祖後?的內涵,只承認?無後而以旁支庶孫為後?一種情況屬於?為祖後?,他對?為祖后?的理解已先在地排除了?嫡孫?。劉寶之所以預先排除?嫡孫後祖?的情況,或與其時大夫以下本無嫡孫承重之制有關,《通典》載西晉庾純議:
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士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祠,下正子孫,旁理昆弟,敘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為之服齊衰。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為宗子服齊衰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11]
庾純提出?嫡孫承重?之制的適用範圍,僅限?王侯有爵土者?,大夫以下,?宜無承重之制?。庾純指出的一個事實是,古今異制,其時?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除擁有世襲爵位的王侯外,此時大夫以下的家內傳重順序是以行輩優先,庶子亦得後父。同一代際的嫡庶之別主要體現為傳重主祭的先後次序,而非傳重資格的有無。《通典》於庾純議下記:?劉智以為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12]劉智晉人,所言當可信。可知?嫡孫承重?服在魏晉時期僅適用於擁有世襲爵位的諸侯之家。魏晉之際,擬制西周五等爵的封爵制度得以建立,西晉擁有五等爵者,地位相當於封建制下的諸侯,爵邑的世襲順序亦比照西周宗法制下的嫡系繼承。諸侯在世襲爵位的同時,還享有建立家廟等禮遇。家廟的傳重順序與爵位的世襲順序一致,所傳之?重?本質上是世襲的政治身分。而在身分不可世襲的大夫以下,嫡孫承重如無源之水。基於這一現實情境,庾純以?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論證嫡孫不應先諸父承重,將?傳重?原則與?承財?統一,要求喪服禮制反映習俗的繼承關係。而習俗中的繼承原則,既構成了劉寶等人從事經典解釋時的歷史語境,也使得魏晉時期的?嫡孫承重?在保留?承重?古義的同時,其適用範圍已不同於經典。
《通典》卷88“孫為祖持重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刊本
?嫡孫承重?服在北朝的施行同樣存在適用範圍上的身分等級問題,卻出現了向士庶普遍通行的傾向。北魏永平四年(),?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13]太常卿劉芳主張終德當同諸孫服期服,論點有二。一、?傳重?意傳宗廟之重,庶人無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14]終德官品不及下士,屬?庶人在官?,無承重之禮。二、魏晉以來已不為嫡子服斬,嫡系子孫並無絕對優先的繼嗣權,?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15]據劉芳議,北魏時,?嫡孫承重?是否下通庶人,存在爭議;其次,宗廟祭祀意義上的承重受到禮的規範,而習俗的家內秩序則以庶叔的尊長地位為先。對此,國子博士孫景邕的反駁也有兩點。一、?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16]二、終德已預士流,?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17]景邕議表明,北魏時確有?嫡孫承重?下通庶人的主張,這一主張的基本論據是喪服一篇本身兼包庶人。其次,孫景邕與劉芳的共識是士以上皆當遵守?嫡孫承重?,爭議在於終德的身分是否屬士。這一點之所以存在爭議,原因在於北魏對官品與《周禮》爵級之間的對應關係,並無明確規定。據《魏書》官氏志,員外將軍屬從第八品下[18],劉芳引晉《官品令》:?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無正從,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19],遂認為終德?官品不及下士?。當時詔書云:?嫡孫為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20]肯定了終德士的身分。由詔書還可進一步推知,北魏時期,?嫡孫承重?服已見著禮令,且下及於士,與魏晉僅適用於世襲爵位的諸侯不同。
如何認識與評價北魏時的?嫡孫承重?服?北魏?嫡孫承重?服制之所以下及於士,甚至還出現了下通庶人的聲音,並不是為了打破?嫡孫承重?服的身分限制,而是禮制的復古背景,導致北魏的?嫡孫承重?比魏晉制度更接近經典。正如前引劉智評魏晉嫡孫承重?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喪服經中的?嫡孫承重?對天子至士一皆適用,並非只為天子諸侯立制。魏晉時期,?嫡孫承重?服制的施行,更多地順應了現實條件而變於古制。北魏在嫡孫承重服上更接近經典古禮,帶有更強的復古特徵。北魏孝文帝漢化改制以來,力圖通過禮制上的?復古?、?宗經?以標榜正朔,?嫡孫承重?服表現出的復古傾向,在孝文帝以來的禮制改革中並非孤例。[21]
唐代禮法中的?嫡孫承重?服仍與封爵世襲掛鉤。《開元禮》編列五服制度,對中古時期的服制變化作了系統整理。五服制度以條目形式排列喪服中的服制規定,在斬衰三年章中加入?嫡孫為祖?一條,表明唐人已將此條服制與有明確經文依據的服制同等看待。[22]《唐律疏議》名例?稱期親祖父母?云:?嫡孫承祖,與父母同?,疏云:?依禮及令,無嫡子,立嫡孫,即是『嫡孫承祖』。若聞此祖喪,匿不舉哀,流二千里。故云『與父母同』。?[23]所言?令?當為封爵令。[24]戶婚?立嫡違法?條疏亦引云:?依令: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准此。無後者,為戶絕。?[25]按:?戶絕?,仁井田陞以為當作?國除?,?戶絕?為後世所改。[26]唐代律令中的立嫡之制,所針對的仍是世襲封爵之家,故立嫡違法條疏云:?立嫡者,本擬承襲。?[27]可知唐代?嫡孫承重?服在適用範圍上主要限於世襲封爵之家,與政治身分的世襲密不可分。[28]
經典所載喪服,與後世喪服制度之間並非連續、無斷裂的承傳關係。以禮經為國法的魏晉時代,對喪服?嫡孫承重?的制度化具有奠基意義。也正因喪服在禮法層面的制度化發展,使經典與習俗的關係開始成為喪服實踐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於魏晉以降的禮議中反復出現。周代宗法封建制下,?承重?意承爵土、宗廟、祭祀之重。中古時期,以封爵世襲為基礎,嫡孫所承之?重?仍大致保留了經典古禮中的實質意涵,這也就決定了?嫡孫承重?服制的適用範圍僅限於特定身分者。而在禮之外的習俗層面,嫡孫並無先於庶叔的承重地位。宋代臣僚無世爵,?嫡孫承重?失去制度依托,卻並未單純隨制度基礎的喪失而消亡。制度條件的失去一方面使禮令條文失去實質意涵,成為具文,最終導致?嫡孫承重?服制在法律層面被更改;另一方面,正因剝離了政治制度背景帶來的身分規約,使得儒學士大夫有條件對?嫡孫承重?的經典禮義進行普遍化的義理重釋,推動?嫡孫承重?向士庶推行,從而形成?嫡孫承重?在宋代的兩重發展。
《唐律疏議》卷6“稱期親祖父母”,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三、尊經與適俗:?嫡孫承重?服制在宋代的兩重變化
宋初喪服制度因襲唐五代以來的沿革變化,對喪服制度進行系統整理,是在天聖五年(),由翰林侍讀學士孫奭?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並見行喪服制度,編附假寧令?[29]。孫奭所訂服制,經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加以通俗化,節取假寧令相關條目相附而成《五服年月敕》,是為北宋喪服的標準制度。天聖七年()頒行的《天聖令》,於喪葬令後附有一份喪服年月,其大題下小注云:?解官給假,並准假寧令文;言禮定刑,即與五服年月新敕兼行。?[30]喪服年月中的服制規定,?基本上是五服年月敕的節略版。?[31]喪服年月?斬衰三年?載:?嫡孫為祖後者,為祖?,小注云:?為曾、高後者亦同。?[32]五服年月敕今佚,文獻所載佚文有?嫡孫承祖?一條,注云:?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33]可知宋代禮令中的?嫡孫承重?服本出《開元禮》,經《開寶禮》、五服年月敕到《天聖令》喪服年月,一脈相承。前述唐代?嫡孫承重?服適用於世襲封爵之家,而由宋初?嫡孫承重?的案例可知,宋初民間實際通行的承重順序是以庶叔先於嫡孫;與此同時,一些士大夫從經典禮義出發,又有將?嫡孫承重?普遍推行於士庶的傾向。直至熙寧八年()修訂?嫡孫承重?服前,這兩種方式皆被官方認可。
首先來看石祖仁的案例。《長編》載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其叔從簡為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34]祖仁為其祖父中立之嫡孫,中立亡後,祖仁並未服嫡孫承重之斬衰,而由其庶叔從簡服斬。庶叔未終服而亡,祖仁疑於所服,故上奏請定服制。祖仁並不懷疑庶叔應先他承重,他不能斷定的是在庶叔未終服而亡的情況下,嫡孫是否還應承重服斬。禮官范鎮以為?經無接服?,謂祖仁當以期服主喪,服除而止。[35]禮官宋敏求駁云:
自《開元禮》以前,嫡孫為祖,雖祖之眾子在,亦服斬衰三年。且前代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古者重嫡孫,正貴所傳,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未及葬,未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又舉葬必有服,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度,請著為定式。[36]
范鎮和宋敏求均默認祖仁在庶叔在世的情況下,不必服承重斬衰。不同的是,宋敏求堅持必有子孫在實質意義上為亡父祖服斬。宋敏求的建議得到採納,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載服制令:?若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亦承重?[37],即本其議。宋敏求認為《開元禮》以前的制度乃嫡孫為祖,雖有庶叔猶承重。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卻透露出庶叔較嫡孫擁有承重的優先地位,是宋初認可的制服方式。但這還不是事實的全部。宋初還存在部分士大夫將經典禮義普遍化、使?嫡孫承重?向士庶普遍推行的趨勢。
史料記載嘉祐七年(),時任建康軍簽書節度判官事劉輝(字之道),請求為死去的祖母解官,承重服斬。[38]劉輝希望在兩位叔父健在的情況下,以嫡孫身分為祖母承重。王贄派去的使者引令文規勸劉輝:?按著令,凡適孫為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據前文對北宋喪服禮令的分析,嘉祐時期,禮令中的?嫡孫承重?服並無?其嫡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這一附加說明,使者所言乃是依據宋初常例對這條服制作出的解讀。使者既引禮令,故劉輝亦引宋封爵令為辯。宋初封爵令因襲唐令而來,前論唐代?嫡孫承重?服主要適用於傳襲封爵者,劉輝則對令文中的嫡系繼承作了普遍化的解讀,言?貴賤雖殊,正適之義則一也。?劉輝的做法得到禮官認可,朝廷亦聽其解官。劉輝等儒學之士,對?嫡孫承重?服制的踐行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楊傑云?有國以來,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也。?劉輝案例的?開創?意義在於以士人身分行?嫡孫承重?,且得到了官方認可。
又有程顥之例。游酢記載,嘉祐年間,程顥在鄠縣主簿任上,?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程顥?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39]州從事遭祖母喪時,庶叔在否,並不清楚。從游酢言?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可以推測此例當是有庶叔情形下的?嫡孫承重?,否則不必特為表彰。游酢之言,雖不免帶有誇張成分,卻表明,一、嫡孫先庶叔而承重在宋初本不常行;二、程顥等儒學士大夫在一定範圍內推動了?嫡孫承重?服制的踐行。這一局面進一步擴大了禮令中的?嫡孫承重?服在法律解釋與實踐層面的分歧,使得服制修訂勢在必行。熙寧八年(),中書禮房對?嫡孫承重?服作了重要修訂:
欲於《五服年月敕》?嫡孫為祖?條修定注詞,云:?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40]
詔從之。注詞肯定了宋初以來習俗中較通行的制服方式,從法律上正式規定嫡孫沒有優先諸父的承重權。中書禮房所奏當本王安石議,見王安石上劄云:
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嫡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嫡子死,非傳爵者,無眾子,乃可於嫡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41]
王安石言封建之法廢,?嫡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可見新法雖標榜周禮,實際的立法施政又有很強的務實與權變精神。王安石的觀點在立論思路上與歷史上的庾純、劉芳並無不同,皆是主張儒家宗法制下的嫡系繼承須以封建世爵制為依托,強調禮的制度條件及其時代性。劉輝、程顥則認為,儒家經典中的宗法嫡系繼承具有超越制度、時代以及身分貴賤的典範意義,應予普遍施行。
《臨川先生文集》書影,再造善本影印紹興兩浙東路轉運司刻本
完整理解注詞內容,還需解釋注詞中有關傳襲封爵者的規定:?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這裡的?傳襲封爵者?,是指慶曆四年()以後可以世襲的宗室王、公爵。宋初至慶曆四年以前,皇子、皇親兄弟可以封王、郡王或國公,但其爵位不可世襲。由於宗室封爵不可世襲,至慶曆四年()正月,荊王元儼去世後,宗室已無一人為王,為藩屏王室計,仁宗大舉新封了?十王?之後。[42]史料表明,這些新封的王、公爵可以世襲,但世襲的方式並不遵循封爵令中的嫡系繼承,而是依照?長者優先?的行輩繼承,?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43],不區分嫡庶。例如,岐王德芳孫、惟敘子從煦於慶曆四年封安國公,從煦卒後,其再從兄弟從古襲爵。從古卒後,又由從古的再從兄弟從式襲爵。[44]宗室?長者優先?的傳爵次序,與士庶的傳重服喪,均體現了依照行輩的繼承原則。[45]熙寧三年(),神宗又改宗室封爵的傳襲方式為父子嫡系繼承,《長編》載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朝廷以為非古……謹按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詔可。?[46]由是,宗室封爵的世襲開始依照封爵令中的嫡系繼承原則進行[47],這就是熙寧八年?嫡孫承重?條注詞?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一句的制度背景。也就是說,熙寧八年?嫡孫承重?條的修訂,從法律上規定了士庶階層嫡孫不先諸父而承重,同時將嫡孫優先諸父的承重權限定在了宗室封爵世襲的範圍內。
?嫡孫承重?修訂後的案例,見《長編》載熙寧八年十月,原知廬州孫覺正以嫡孫身分解官為祖母服喪,其時孫覺的叔父尚在,有司據新令,以孫覺不當解官,遂使孫覺改知潤州。[48]熙寧八年修訂的?嫡孫承重?服制成為有宋定制,《慶元條法事類》載服制令:?諸嫡子死,無兄弟,則嫡孫承重。若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亦承重。……無嫡孫,則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眾長孫承重。即傳襲封爵者,不以嫡庶長幼,雖有嫡子兄弟,皆承重,曾孫、玄孫亦如之。?[49]對士庶而言,禮令中的?承重?的確如滋賀所言,已轉義為僅表示三年重服的喪服術語。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禮法層面雖如此規定,而士大夫將?嫡孫承重?服制普遍推行的想法並未消失。在一些士大夫群體於士庶階層倡興宗法的背景下,?嫡孫承重?服經重新闡釋與實踐,獲得了更高的普遍性。以朱子為代表,《家禮》中的服制便刻意採用了經典古禮中帶有宗法背景的?嫡孫承重?。元代以降,伴隨《家禮》的官方認可與民間流布,士大夫的家禮實踐獲得了向士庶普遍推行的契機,深刻影響並塑造了元明清代禮法與習俗中的制服與承祀方式。
四、朱子《家禮》及其影響下的元明清代?嫡孫承重?服
熙寧八年修訂的?嫡孫承重?服,並未被元明清代的禮法服制所繼承,從《元典章》、龔端禮《五服圖解》到《大明集禮》、《孝慈錄》、《大清通禮》、《大清律例》中的服制,?嫡孫承重?皆未延用熙寧八年修訂後的注詞規定。[50]這是因元明清代禮律中的?嫡孫承重?服承自《家禮》的緣故。《家禮》喪禮?斬衰三年?條下云:?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為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51]又《家禮》喪禮?立喪主?條:?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52]皆明確以嫡孫承重主喪。楊復注進一步揭示出朱子的立制之旨: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為後,故父為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
先生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為父後者乎?[53]
朱熹《家禮》卷4“斬衰三年”,宋刻本
楊注本朱子與郭子從問答之語。[54]郭子從提出,大宗法廢後,長子、庶子皆可為父後,具有同等的繼嗣地位,?子各得以為後?。與庾純、王安石等堅持禮的制度基礎不同,朱子在知古禮的制度基礎不存的前提下,仍主張保留古禮的形式,體現了孔子?愛禮存羊?之意。不過,朱子主張?愛禮存羊?,非僅自足於從形式上保留古禮,《家禮》中的?嫡孫承重?服制,以《家禮》的宗法祭祀構想為背景,楊復注言:
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係,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55]
楊復指出,宗法為《家禮》之大義所係。《語類》載朱子論家祭儀:
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者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卻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卻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卻有古宗法意。[56]
《家禮》云:
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桌。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57]
?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故嫡長死,庶子亦不得先嫡孫而後父。也就是說,?嫡孫承重?并非獨立存在的喪服制度,而是與承祀繼嗣相輔相成。早在朱子之前,張載、程頤、程顥等宋儒已力倡復興宗法。在宋代無世卿世祿的現實條件下,宋儒宗法學說的一大特點是剝離了經典古制中世爵的制度背景,使宗法得以下及庶人。二程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58]程頤云:?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59]張載言:?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60]可知宋儒提倡宗法,面向的群體是廣泛的士庶階層。與中古時期宗法適用於特定身分者,及其規範士族政治身分傳襲的主要功能不同,宋儒宣導宗法復興,要在發揮宗法的收族功能,重塑士庶的家族生活秩序。[61]元明清代禮法中的?嫡孫承重?服制,未延續宋代禮令中的規定,而是繼承了《家禮》所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群體的家禮實踐,其意義須放在宋以來的思想背景下才能獲得恰當理解。
元代民間喪服在制度和文獻層面都與《家禮》存在莫大淵源。《元典章》所載五服圖云:?若嫡孫承祖,同父母?[62],元人龔端禮《五服圖解》亦云:?祖父母,齊衰不杖期。若父先卒,己承重,父母服同。?[63]《元典章》與《五服圖解》使用了一種菱形宗枝圖。吳飛指出:?在現存的資料中,最早的菱形宗枝圖出現在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的喪禮部分和楊復的《儀禮圖》中。宋代以降,特別是明清,官方和民間都廣泛使用這一五服圖。?[64]需進一步說明的是,《元典章》、《五服圖解》以及元明清官方、民間廣泛使用的宗枝圖,與黃榦、楊復禮圖有所區別,其源頭應是宋末元初的民間日用類書。[65]《家禮》原本應該沒有五服圖[66],元初建安所刻纂圖集注本《家禮》始增入五服圖[67],《元典章》、《五服圖解》中的宗枝圖畫法正與此相同。此種畫法的五服圖最早出現在宋末至元初的幾部民間日用類書,如《事文類聚》、《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事林廣記》中[68],其中的喪服制度皆承自《家禮》。《事文類聚》編者祝穆、《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編者劉應李,均深受朱子學影響,對《家禮》的採錄並非偶然。《元典章》由坊間編刻,《五服圖解》為龔端禮私撰以切合時用之禮書,其中的五服圖及喪服禮制很可能即本自這些民間日用類書,其制度源頭正在《家禮》。龔端禮於《五服圖解》言:?朱文公《家禮》所載前項喪服,皆案古宜今,士夫家多遵此而為之。?[69]《五服圖解》撰成於至治二年(),是元代私人編集的代表性禮書。泰定年間,編者龔端禮又本五服圖增補更通俗的易曉之圖,云:?愚思此集乃當今官民必用之文,復慮世人不克周曉,故盡心窮理,按古增劃易曉之圖。?[70]《家禮》喪服制度的流行程度,可見一斑。《五服圖解》還揭示了龔端禮等元代士人如何從義理上詮釋《家禮》中的宗法嫡庶關係,《五服圖解》嫡庶義子之圖下云:
其婦所產之長子,謂之嫡子。蓋其祖父一點之元氣,竟傳其嫡。而嫡子所產之子謂嫡孫。其父有疾、故,即嫡孫為之祭主。書曰續祖繼體、嫡嫡相承,其此之謂乎?是以神像、容貌、言語、性慧多有相類,故為嫡子而父斬衰、母齊衰,皆服三年之重服。其次之子謂之眾子,雖一父母所生,為其元氣散亂,不得其嫡,而父母惟以期服。[71]
龔端禮以?氣?的理論解釋嫡庶之別,使宗法嫡庶脫離周代封建制度,成為更具普遍意義的承祀原則。滋賀秀三關於承祀與承財同一性的重要論述,是以財產的兄弟均分與繼嗣承祀的兄弟平等,同為?父子兄弟、本同一氣?這一自然觀念的反映。龔端禮從?氣論?角度對兄弟關係作了完全不同於滋賀的詮釋。宗法繼嗣作為?天理即自然?意義上的?自然?,使?嫡孫承重?以更強的普遍性,成為塑造習俗的觀念力量。伊沛霞從《家禮》的刊刻與流布、官方地位的確立以及民間改編等角度,再現了《家禮》在明清社會中的影響,指出,至十六世紀,人們已廣泛期待士大夫以某種基本方式遵守《家禮》,對《家禮》的遵守亦被視為文士地位的標誌。[72]喪服制度由於關聯到官員丁憂、恩蔭等公法領域,因此下面先從官方禮令的角度分析明清時代的?嫡孫承重?。
明清禮律中的?嫡孫承重?服制規定不僅在文獻、形式上,且在實質意義上因襲了《家禮》。明清士人在喪服實踐中遵行?嫡孫承重?,史料中頗不乏其例。明康海甘節吳先生墓志銘云吳傑:?值祖與祖母繼歿,先生以嫡孫承重,三年之喪,哀痛備至。洎除服,仲父析居,季父上京矣。?[73]李東陽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何公墓志銘載:?郴州何公廷彥,以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歸十有八年,卒於家,其長孫孟春承重當終制,乃具衰絰請於予……子三,說長而賢,其卒時也,時論惜之。次言、次誾。?[74]何孟春承重服斬時,其叔父何言、何誾應尚在。尹襄長寧訓導劉君墓志銘載:?長寧司訓劉君之卒也,主其喪者,其孫鄉貢進士孔愚,以適承重也……男三人,冔其長也,次昇,次旦,邑庠生。?劉茝卒時,主其喪者為嫡孫劉孔愚,其時孔愚叔父昇、旦應尚在,孔愚以銘請於尹襄。[75]清陳兆崙作劉元燮墓志銘云:?某年某月承重孫鐸將奉先生柩,隨諸叔卜兆於某山某原,前期請為之銘。?[76]蔡新撰其伯兄行狀云:?雍正丙午,先大父資政公司訓安溪,得末疾。先生自家奔侍,時新偕仲叔兩父省試未回……踰月,資政公卒,先生為適孫承重三年,無違禮。?[77]又,茹綸常撰資政大夫慎菴張君墓志銘:?時應恆以承重,與其叔父俱丁太夫人憂,將以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太翁與太夫人柩,合葬於南村原。?[78]在以上明清墓志、行狀中,?嫡孫?地位突出,既需承重服斬,往往也是操辦喪事、請銘之人。這與前文介紹的宋朝情況,已有了很大不同。
?嫡孫承重?作為喪服制度,既著之禮律,又受蔭補、丁憂等公法制約,對士人階層的喪服實踐具有較強的規範性,與此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至民間禮俗。清初學者萬斯大言:?今天下喪禮廢壞,獨嫡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稍見古人為後之義。?[79]語本萬斯大評清人張文嘉《齊家寶要》。張文嘉於康熙年間輯撰通俗日用類儀注《齊家寶要》。是書本《書儀》、《家禮》,參以時制而成,其中關於?嫡孫承重?的服制規定,與《家禮》相同。惟喪禮?立喪主?條下云:?長子為主人,無則長孫或次子為之。此古人重嫡之意。?[80]張文嘉雖云?長孫或次子為之?,實則更強調長孫的優先地位,其?嫡長承重?條下即云:?重者,主也,謂主喪也。?[81]饒是如此,萬斯大依舊強調不得以次子主丧。而當時習俗應不乏以年長之次子主喪者,萬斯大言:
友人吳秉季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嫡孫為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82]
吳秉季與萬斯大所爭者,非為嫡孫是否應承重,而在承重是否應即主喪。吳秉季提出?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言?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因世俗多有以年長之次子主喪;萬斯大則從?承重?的原理出發,強調?承重?與?主喪?的同一性而力主只以嫡孫主喪。如果說?嫡孫承重?服制有著禮法上的依據,行之無疑,那麼唯嫡孫主喪可以說體現了士大夫按照?嫡孫承重?的經典禮義來進一步整齊、塑造民間禮俗的努力。
由《家禮》到士民禮儀,由士民禮儀到家國禮法,再由禮法到禮俗,?嫡孫承重?並未延續北宋禮令中的變化趨勢,且比魏晉時期的?嫡孫承重?具有更強的普適性。在此,經典對後世禮法、習俗的形塑,顯示出經典之為觀念來源,並不必然為自身歷史背景所限的一面。古今的制度條件雖然懸隔,經典中的宗法繼嗣觀念卻可經由新的義理詮釋,加以普遍化,成為規範生活秩序的通則。然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無論經典禮義還是禮法條文,當其實踐之際,都不能無視習俗所生發的現實情境;?緣情制禮?、?因時制禮?,亦是儒家禮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明清之際的禮學轉向中,正是對經典自身歷史語境的考證與重建,形成了質疑《家禮》的批判性立場。下面透過清代學者在?嫡孫承重?服制上的相關爭議,從學術思想層面概見?嫡孫承重?服制背後,經典與習俗之間仍未消解的內在張力。
五、經典與經驗:古禮考證興起下的服制論議
相較載之禮律的喪服制度,民間喪葬、祭祀等習俗性活動中存在的地域差異和變化,有的已超出禮令規約的範圍,?嫡孫?在私法領域的位置也更為模糊。[83]例如,在主喪者的確立上,既有以嫡子、嫡孫為喪主,也有上文吳秉季?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之論。在宗族祭祀禮儀中,既有不少宗族譜採用《家禮》影響下的宗法祭祀[84],也有因應不同實踐需要而採取的祭祀模式。[85]對於身處不同禮儀生活方式的人們來說,?嫡孫?的地位和意義並非理念中的整齊劃一。正是在面向庶民及應對複雜實踐的過程中,產生了對《家禮》的不同改編與質疑。[86]張壽安指出明清禮學的一大轉折,是從?家禮學?轉向以經典、古禮考證為內容的?儀禮學?。[87]周啟榮將清代考證禮學放在以?禮?為核心的思想文化變革——儒家禮教主義興起的視角下加以理解。[88]他們的研究揭示,清代考證禮學具有關注禮制儀節等經驗秩序,並從經典自身視域出發推考古代禮制的取向。[89]與《家禮》強調禮儀、禮義之為?理?的普遍性不同,古禮考證凸顯出的是?古今之別?。考證禮學發揮其經世效用的原理在於,對古代與當下各自具有的特殊性都給予如其所是的精微體察,進而如張壽安所言:?從清代禮學者的禮經考證與新詮中,我們看到的是清儒對個人之情、家族之情的重視,甚至包括相對於家族而言的個人之私體、相對於皇權而言的家族之私體等,皆備受重視並給予正面價值。?[90]古禮考證所帶來的並不是簡單回到古代,而是回到?禮?的經驗世界。
因此,在清初毛奇齡與萬斯大關於?嫡孫承重?的分歧中,萬斯大立足?古今之通義?,而毛奇齡則強調?承重?在經典時代的歷史社會基礎。萬斯大理解?承重?的核心是?承嗣?,?重?的本質是?正體之重?,?承重?的禮制意涵是:主喪、主祭、服斬:
故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為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為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為祖後也。為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為父同,此承重之義也。
重為先祖祭祀之重,父死子繼,豈獨非承?今以子死孫承謂主祖喪為承重,是重之義專指祖喪矣,亦知孫為祖後而服斬,乃代其父為喪主,非關承重乎?曰五服莫重於斬,唯子為父服之,孫為祖本齊,今代父服斬以為喪主,不謂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謂祖喪服斬之非重,第言禮必本於經,?承重?之稱生於?傳重?,?傳重?之義由乎?主祭?,即安得專指孫主祖喪而言承重也?[91]
萬斯大《學禮質疑》“適孫承重二”,皇清經解本
萬斯大認為,?正體?傳承暨宗法性的嫡系繼承,乃繼嗣的古今通則。前文指出,將這一原則在真正意義上予以普遍化,始於宋儒、尤其是倡興宗法的學者。萬斯大擁護《家禮》,是這一思路的繼承者。萬斯大層層論述了?承重?應包含主喪、服斬、主祭三個方面。前引滋賀秀三認為,明清時期,?承重?一詞已失去宗祀意涵,轉訛為指稱三年重服。至少在萬斯大看來,繼嗣承祀仍是?承重?的實質規定。而就前述史料所見士庶喪禮實踐來看,?嫡孫承重?服斬、主喪、主祭合一的模式依然存在。無論是在觀念還是實踐層面,都不能簡單斷定?承重?已變為單純的服制術語。再看與萬斯大相近的觀點,沈彤云:
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注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啟殯而朝,卒哭而祔,練而祭,喪禮有行於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康成雖專以?重?為宗廟,然言廟則自包寢,故承重之禮,庶人與士大夫同。《魏書》禮志孫景邕等三議皆當,可從也。[92]
沈彤亦強調?承重?具有承祀、主喪雙重意義,且為士庶通行之禮。不過,沈彤從制度角度對?承重?下及庶人的論證,並不成立。廟雖有寢,但並不包括無廟而寢祭的庶人之寢。有理由認為,沈彤作為清初重要的《儀禮》學家,之所以論證失當,實本?承重?下通庶人這一先見立論。又,黃以周《禮書通故》言:
凡為後者,正體與傳重並重,其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適子有廢疾是,有傳重而非正體者如庶子為後、庶孫為後是,皆不得加服三年。惟正體又將傳重,乃為加服,此為上下通制。淩次仲力主杜說,必有宗廟、土地、爵位、人民而後謂之重。五世則遷之小宗已為無重可傳,如其說,古立小宗法,亦為過舉矣。[93]
黃以周駁淩廷堪以有宗廟、爵土方可謂?重?,強調?正體?與?傳重?並重,以之為?上下通制?。《禮書通故》為晚清禮學殿軍,但此處論述及其對淩廷堪的反駁,都不無模糊處。經文中,?士?亦屬可有宗廟、爵土階層,即此而言,淩廷堪並不反對無大宗之士可以承重。而黃以周所說?上下通制?是否兼包庶人,卻未言明。從黃以周反對淩廷堪專以宗廟、爵土為說,可知黃以周當是認為?承重?下通庶人。如前所述,這是宋以後才開始實現的情勢,對黃以周的立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萬斯大、沈彤、黃以周皆是清代著名禮學家,對於經典研究傾注了極大心力,而在他們的經學解釋中,多少暗含了?宗法下及庶人?這一後置視域。肇自清初,一些以經典古禮反對《家禮》的學者,開始主張回到經典自身語境,強調?承重?在其時代的社會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毛奇齡論?承重?云:
古無?承重?名,但有?傳重?、?受重?二名,謂祖父以宗社之重傳之於我,而我從受之,則此祖、此父皆先君也。……是今之?承重?,實從?傳重?與?受重?二名而誤稱之,而今之孫為祖父母三年,實由先君與先太后之服而誤服之者也,原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承之,謂之承重孫也。但曰?為父後?,?為祖後?,則仍是?承重?之別名,士庶有何後而子為之,孫又為之?[94]
毛奇齡《經問》,皇清經解本
毛奇齡是清初批判《家禮》及其宗法背景的重要學者,對萬斯大的宗法學說亦予尖銳批評。[95]毛奇齡將?重?定義為?宗社之重?,?承重?範圍限於有土之君。由承重?原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承之,謂之承重孫也。但曰『為父後』,『為祖後』,則仍是『承重』之別名”可知,毛奇齡同樣強調?承重?的承嗣意涵。與《家禮》、萬斯大不同的是,毛奇齡質疑宗法繼嗣原則超時空的普適性,並以制度基礎對其適用性而言更為根本。與毛奇齡觀點一致,李紱云:
蓋自封建廢而諸侯不世國,命卿廢而大夫不世家。公卿嫡長之子孫夷於黎庶,固無重之可承。既非世國、世家,即不能別立大宗,亦無重之可承。既非世國、世家,即不能別立大宗,亦無重之可繼,烏有所謂?承重之孫?也哉?長子死而嫡孫承重,始行於吾鄉先達劉狀元煇,祖母卒請承重,事下禮部,宋時士大夫不習於宗法而好言宗子,遂從所請,自是以來,嫡孫有叔父而輒稱承重,不知古禮之不然也。近日鄞縣萬氏斯大著《學禮質疑》,中宗圖頗為明備,亦未嘗深思古義,不知其所論著皆無用於今之世者。[96]
李紱亦以?重?為世國、世家之謂,直言萬斯大之宗法學說?皆無用於今之世者?。李紱注意到了?嫡孫承重?向士庶普及始於宋,並歸咎於宋儒?不習於宗法而好言宗子?。再看其他考證學者的論述,淩廷堪《禮經釋例》言:
考喪服·斬衰三年章?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嫡子卒,嫡孫為祖後為三年之服,謂之承重也。然此唯封建之世有之,《通典》言之甚詳……今律有承重之文,以《通典》考之,亦指世襲之家有後者言之。知禮者稀,即律文亦不易讀也。陋儒據《家禮》,每於士庶人家行此,且使諸父在其下,則全非禮意矣。[97]
又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
嫡孫承重之服,主有宗廟者而言,劉芳之議自不可易。今庶人無爵而以孫上陵諸父,非禮意也。[98]
又陳祖範《經咫》言:
為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為後之子亡則嫡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宗法廢,士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為後不為後之分,既已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曰?是禮也?,禮果然乎哉?[99]
淩廷堪、錢大昕、陳祖範再次展現了對於古禮的歷史語境化理解,以爵土、宗廟等制度詮釋?重?,凸顯了宗法承嗣的歷史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一面。對古禮特殊性的揭示、高度經驗化的思維方式,從兩方面構成了考證學者的實踐主張:一、從古今之別的角度,批判《家禮》及其影響下的禮俗之?非禮?,如以上淩廷堪、錢大昕、陳祖範無不批評當世?嫡孫承重?有違經典禮義。二、並非制度性地回到古禮,而是要求體察當代禮儀實踐的現實處境。《四庫總目提要》評陳祖範《經咫》?不以古制違人情?[],評毛奇齡《辨定祭禮通俗譜》?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托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釐然有當。?[]在?嫡孫承重?問題上,萬斯大等與毛奇齡等的差別,重點不在誰更實用,誰更適應現實禮俗。如前所述,在宋儒的努力及《家禮》影響下,?嫡孫承重?在士庶中的施行已不鮮見;上述淩廷堪等論亦印證了宗法性?承重?對於習俗的深刻影響,成為引發他與錢大昕等著言反對此禮的直接原因。萬斯大等與毛奇齡等的論爭,於學理上更清晰地呈現了歷史上儒家內部關於?嫡孫承重?服制的固有爭議,分歧的根源仍在於如何理解?禮?與實踐生活的關係,?禮?是一系列普遍化的規則,還是?緣情而制?的實踐技藝。
六、結論
喪服小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鄭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繼祖為?正體?,體現了周代宗法繼承原則中的?嫡嫡相承?。[]經典古義中的?承重?意味著繼承爵土、宗廟之重。魏晉至唐代,嫡孫所承之?重?大致保留了古禮之實,?嫡孫承重?一般只行於封爵世襲之家,在適用範圍上受到身分等級的限制。而在習俗領域,嫡孫並無先於庶叔的承重地位。宋代臣僚無世爵,品官家廟未曾普遍建立,?嫡孫承重?失去制度依托。北宋熙寧八年的服制修訂,從法律上確立了庶叔先於嫡孫的承重權,反映了禮法對習俗承繼方式的適應。但也正是政治制度造成的身分規約在宋代的消失,?嫡孫承重?獲得了超越制度條件、向士庶推行的契機。藉由士大夫對宗法原理的普遍性重述及其家禮實踐的推廣,元明清時期,?嫡孫承重?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向士庶階層的推行,深刻影響了禮法與習俗中的承祀方式。與此同時,經典與習俗之間的張力並未消失。習俗的複雜多元始終挑戰著單一原則的合理性,而考證禮學恰恰是通過經典研究的方式,重新彰顯了禮的經驗特徵。對?嫡孫承重?服制的歷史考察,展現出其實踐的複雜面。從這一歷史圖景出發,回到文章開篇所提繼嗣原則問題的爭議。仁井田陞指出,在中國古代祭祀繼承人的選定上,?嫡系主義?與?行輩主義?兩大類型在不同時代互有消長。?嫡孫承重?服制的歷史變遷更支持這一描述,但還需作更深層的解釋,並對滋賀秀三的理論加以回應。
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不僅是社會經濟關係的反映,亦是士大夫從觀念上進行塑造的結果。經典之為經典,在於其中的原理能夠被普遍化,並因此超出制度條件的約束。歷史上,繼嗣承祀與財產繼承原則並不總是保持一致。儘管漢以下至清代的財產繼承基本採用諸子均分,但在繼嗣承祀問題上,嫡系繼承仍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則。
滋賀秀三極富洞見地提出了從根基上把握古代繼承問題的重要理論。與此同時,?禮?之於古代生活的意義,有時正潛藏在實踐問題的複雜與觀念的衝突之下。?嫡孫承重?服制的歷史揭示,如何處理經典、禮法與習俗的關係,歷史上既存在不同思路,也反映出對?禮?的差異性理解。其一是將?禮?視同?天地自然的理?,宋明理學很大程度上發展了這一禮即自然的觀念。理學士大夫雖然能夠推動普遍之?禮?形塑禮法與習俗,卻不能抹去習俗的差異性、替代習俗的自發性。從庾純、劉芳到王安石等,再到清初考證學者,他們強調古禮的歷史背景與特殊性,其實是從根本上將?禮?理解為?人為之物?。?自然?即不待人為的生之自然,自然情感或自發生成的習俗,從這一意義上說,?禮?是非自然的,是人類在時空中的歷史創造。中國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在經典、習俗與禮法三者交互中展現出的複雜性,亦需在不同禮觀念的對話下獲得深層理解。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
唐·蕭嵩等,《大唐開元禮》,北京:民族出版社,。
《天聖令》,《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宋會要輯稿》,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慶元條法事類》,戴建國點校,《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1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宋·楊傑,《無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王安石全集》第6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宋·程顥、程頤,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宋楊復、劉垓孫注,《文公家禮集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印。
宋·祝穆,《事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據明萬曆刊《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影印。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據元後至元本影印。
宋·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刻本影印。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陳高華、張帆、劉曉、黨寶海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元·龔端禮,《五服圖解》,《續修四庫全書》第9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元杭州路儒學刻本影印。
明·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
《大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楊一凡點校,《孝慈錄》,《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3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大清通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鄭秦、田濤點校,《大清律例》,《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編第1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明·康海,《對山集》,《續修四庫全書》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萬曆十年潘允哲刻本影印。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明·尹襄,《巽峰集》,《明別集叢刊》第2輯第13冊,安徽:黃山書社,,據清光緒七年永錫堂刻本影印。
清·陳兆崙,《紫竹山房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清·蔡新,《緝齋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嘉慶刻本影印。
清·茹綸常,《容齋文鈔》,《續修四庫全書》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萬斯大,《學禮質疑》,《清經解》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
清·張文嘉,《齊家寶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冊,濟南:齊魯書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清·沈彤,《果堂集》,《清經解》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
清·黃以周著,王文錦點校,《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
清·毛奇齡,《經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清·李紱,《穆堂別稿》,《續修四庫全書》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影印。
清·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點校,《廿二史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淩廷堪著,彭林點校,《禮經釋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清·陳祖範,《經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二、近人論著
(日)仁井田陞3《支那身分法史》,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日)仁井田陞著,牟發松譯《中國法制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仁井田陞、牧野巽著,程維榮譯「故唐律疏議」制作年代考,《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魏晉隋唐卷》,北京:中華書局。
(日)滋賀秀三承重について,《國家學會雜誌》71卷8號。
(日)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
丁淩華《中國喪服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常建華《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馮爾康《中國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閻步克《服周之冕——周禮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北京:中華書局。
皮慶生唐宋時期五服制度入令過程試探——以喪葬令所附喪服年月為中心,《唐研究》1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吳飛五服圖與古代中國的親屬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2:。
(日)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資料篇》,東京:東洋文庫。
(日)小島毅《中国近世礼の言說》,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日)井上徹、遠藤隆俊《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臺北:稻鄉出版社。
(美)周啟榮著,毛立坤譯《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倫理道德、儒學經典和宗族為切入點的考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Patricia,BuckleyEbrey..ConfucianismandFamilyRitualsinImperialChina:ASocialHistoryofWritingaboutRites.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Timothy,Brook..“FuneraryRitualandTheBuildingofLineagesinLateImperialChina”,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9.2:-.
Classics,CustomsandStatutes:AHistoricalInvestigationOn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
FengCh’ien
Abstract
AbouttheprincipleofsuccessionandsacrificeinancientChina,therearedifferencesbetweenNiidaNoboruandShuzoShiga.NiidaNoborubelievesthatintheselectionofsacrificialheirs,thetwomajortypesof"linearism"and"seniority"havetheirowngrowthanddeclineindifferenttimes.ShuzoShigabelievesthatafterQinandHandynasties,the“seniority”hasalreadyreplacedthe"linearism".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hasprovidedanimportant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theprinciplesofsacrifice.FromWeiJintoTangdynasty,inheritancerightembodiedthetitleofnobilityandlandownership,andmainlyapplicabletothehereditaryfamily.Becauseofthevanishingof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for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intheSongdynasty,thepriorityofthesenioritywasestablishedlegallyintheeighthyearofXining().Atthesametime,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hadgottheopportunitytospreadtothe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jmwc.com/zcmbhl/172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