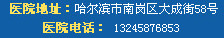古代声乐文化生态如何促进宋词演唱与发展
——以笙为例
董希平
摘要
具有文学和音乐双重属性的宋词,其演唱与发展既有自身内在的文学规律,又受其所处声乐文化生态影响。词倚声而填,和乐而歌,不同乐种的风格倾向、不同乐曲的审美差别、不同乐器的选择使用乃至不同歌者的临场处理均会对歌词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会凝定于歌词并成为传统流传下去。以笙为例,这种古老乐器在周秦之际沉淀了浓厚的礼乐色彩与图腾意味,在宋代借助丰富的物质基础,以其种类多、形制繁的特征而介入宋词表演,进而从多方面强化了宋词宴会表演属性和喜庆色彩。这种影响也最终在歌词中凝定下来并成为歌词传统的一部分。笙的内涵与演奏对宋词演唱的影响,是中国声乐文化促进宋词发展的一个范例。
关键词
声乐文化;笙;宋词演唱;发展
作者简介
董希平(—),男,山东莱阳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词学研究。
词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得益于其歌词的文字功能与音乐属性。歌词倚声而作并与歌舞相伴而传,与声乐文化呈现共生关系。声乐文化的若干影响在促进词体演进的同时,又凝固于歌词本身而成为词体的一个有机部分。以声乐文化组成部分的乐器而言,其演奏的乐曲是歌词赖以生存的基础,因其结构改进引起的乐曲风格变化,则是歌词发生新变的重要动力,其长期凝定的情感色彩,更影响到歌词属性。笙是宋词演唱所用乐器中结构比较简单的一种,但其作为声乐元素对宋词演唱的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周秦以来累积于笙的礼乐色彩与图腾意味使其成为宴饮中宋词演唱的推动力,其嘹亮的音色与流畅的旋律促成了宴饮曲词尤其是寿词的流播,笙自身也进而成为歌词的重要意象。笙从推动歌词流播的外在声乐力量进而渗透至宋词文本本身,成为歌词本体的一部分。由声乐因素而形诸文字,这是笙影响歌词创作与演唱的内在机制。笙可谓中国声乐文化促成宋词演唱与发展的一个范例。
一、从周到唐:笙之礼乐色彩与图腾意味
笙的发明,可追溯至女娲时代。据撰于先秦的《世本》所载,女娲与随合制该乐器,笙苗、笙斗、笙簧构成笙的主体,女娲作笙簧,随作笙。后《世本》亡佚,汉人所引该著内容记录了这一情形。
笙攒竹而成,人们以其形像凤凰息止之时,如万物初春生发之象,因此多在阴历正月吹奏。笙有大小,多依笙簧数量与笙苗长短而分。《周礼》春官宗伯下设笙师,负责教授“龡竽、笙”等乐器。《尔雅》辨别大小笙:“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晋人郭璞对前者的解释是:“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后者则是:“十三簧者。”许慎《说文解字》对“笙”之礼乐色彩与图腾意味总结曰:“笙,十三簧,象凰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谓之笙。大者谓之巢,小者谓之和,从竹,生声,古者随作笙,所庚切。”在保持礼乐色彩与凤凰图腾意味前提下,笙之形制、种类随时代与音乐演进而有所改易。比如,南朝沈约修《宋书》时,笙、竽构成八音之中匏类乐器,前者宫管在诸管中央,十九至十三簧;后者宫管在左旁,三十六簧。三十六簧的竽因体型过大不便演奏而少有人用,沈约言之失传。
笙外形如凤凰来仪之状,又有春天万物生发之相;笙簧与笙苗合作发声,呈线性音色兼有清亮浑厚特性,易与其他乐声融合,故笙在远古已颇受欢迎。大舜之时,乐官夔指挥庙堂祭祀乐舞,笙即是与钟磬次第演奏以伴百兽舞蹈的乐器。笙和镛(大钟)次第演奏,鸟兽相率而舞,呈现礼备乐和气象。笙在周代非常流行,是乐器中的贵族。它与钟、磬、琴、瑟同奏,契合无间;与万舞、夷舞、翟舞协作,展示周代礼乐和谐有序的面貌。宴会之上,笙是宾主同乐、表达情志、共尽酒兴的媒介,笙备君子之德,既能与众和,又能卓尔不群;它能与其他乐器合奏,又是礼仪中重要的独奏乐器。乡饮酒礼,笙独奏与歌唱相间而行,一歌一吹:“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周人燕礼之中,除上述一歌一吹之外,又有笙乐三连奏:“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上述六支笙曲,列入《诗经·小雅》,为有目无辞的“六笙诗”,是当时宴飨宾客的通用乐曲。
仅就乐器属性而言,笙音域宽广,乐声适应性强,在传统乐器中属于功能强大的类型,独奏、伴奏之外可领奏,亦可主奏,是名副其实的“五声之长”:“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春秋时“滥竽充数”的故事,显示当时可以有人规模的笙乐队合奏。笙在礼仪、宴飨中的高贵地位不断凸显,它作为栖凤之象的神圣图腾意味也不断强化,即凤凰不死的图腾意象使得笙更多出现在寿诞宴饮歌舞场合,成为喜庆长寿之象的基础。周穆王乘八骏拜访西王母,奏乐讴歌中就有笙在:“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修仙成功的王子乔,其标志性习惯就是“好吹笙,作凤凰鸣”:“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山首焉。”此后,缑山鸾笙一直是歌舞中不衰的话题。
汉魏以降,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为普及,吹笙既是文人之雅事,亦为文人热衷歌咏。笙的材质、演奏、形貌更被晋人赋予神秘华贵色彩,王廙《笙赋》描述笙制作之精美:“其制器也,则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悬崖之绝岭,邈隆峰以崇高,延修颈以亢首,厌瑶口之陆离。舞灵蛟之素鳞,衔明珠于带垂。弱舌纸薄,铅锤内藏。合松臈以密际,糅彤丹以发光。”夏侯淳《笙赋》则凸显吹笙之优雅与笙乐之动人:“嗟万物之殊观,莫比美乎音声。总众异以合体,匪求一以取成。虽琴瑟之既丽,犹靡尚于清笙。尔乃采桐竹,翦朱密,摘长松之流肥,咸昆仑之所出。抑扬嘘吸,或嗋或吹。厌枯挹按,同覆互移。初进飞龙,重继鹍鸡。振引合和,如溃如离。若夫缠绵约杀,足使放达者循察。通豫平旷,足使廉规者弃节。冲灵冷澹,足使贪荣者退世。开明爽亮,足使慢惰者进竭。岂众乐之能伦,邈奇特而殊绝。”潘岳《笙赋》则颂笙醇厚风俗、导人向善之德:“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乐所以移风于善,亦所以易俗于恶。故丝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群声之清;惟笙也,能总众清之林。卫无所措其邪,郑无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乐,不易之德音,其孰能与于此乎!”
南北朝时期,胡乐器在中土广泛流播,传统笙的使用顿显寥落。至唐朝,笙已成为普通乐器。唐高祖李渊飨宴用隋九部乐,唐玄宗李隆基分立、坐二部,立部伎凡八部,因无乐器使用记录,笙的情况不可得知;坐部伎凡六部,唯《燕乐》有乐器记录:乐用玉磬一架,大方响一架,搊筝一,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大箫一,小箫一,正铜钹一,和铜钹一,长笛一,短笛一,楷鼓一,连鼓一,鼗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清乐凡四十四曲,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四夷之乐,所用各种笛、琵琶、鼓,琳琅满目,然仅《高丽乐》《龟兹乐》有“笙一”而已。为教坊所辖散乐和龟兹乐、来自河西的“胡音声”一起“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其所用乐器亦无笙影。
唐德宗李适贞元中,骠国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以其舞容、乐器异常”,到成都时,当时的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乃图画以献”,而令韦皋惊讶的众多骠国乐器中有品种丰富、形制多样的笙,其中有保持中土传统的“大匏笙二”“小匏笙二”,有骠国独有的“三角笙”“两角笙”。故“礼失而求诸野”这句话放在笙身上,较为合适。远古高贵典雅的名器,已衰落到如此境地,笙的经历可谓传奇。
但这传奇显然尚未结束,稍后的10世纪,词开始勃兴,在宋代歌舞表演中,笙再次流行于雅乐和俗乐之中,从庙堂到市井,从祭祀到宴饮,笙以其多形制、多种类、多功能的特点,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乐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宋词演唱衰歇的13世纪。
二、声乐与歌词:笙在宋词演唱中的使用
宋代是周以后笙的又一个黄金期。笙音极强的融合性,笙本身积淀已久的龙凤图腾意味、礼乐色彩以及与箫鼓合作产生的喜庆氛围,使它受到宋代歌舞的空前欢迎,而且宋代几乎所有乐种,如登歌雅乐、教坊俗乐、军乐、胡乐等均有它的存在——笙一时间成为宋人歌筵中最普及的乐器。
笙应用于祭祀、朝会等国之大典礼仪,宋真宗朝已非常规范。宋景德三年(年)八月,真宗按试宫县、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对于太常乐工的精熟非常满意,这其中就包括笙的演奏:“上御崇政殿张宫县阅试……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宋神宗元丰二年(年),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则有巢笙、和笙各二人吹奏。
南宋初年战乱之后,国家大典中笙的使用恢复北宋的规模与细密分工。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年)郊祀,登歌用“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宫架则用“巢笙及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竽笙十”。俗乐中笙的使用更普及。宋教坊十三部色,其中之一即为笙色,可见其规模之大。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言:“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色有色长,部有部头。”
宋代宫中乐团云韶部所用乐器有“琵琶、筝、笙、觱栗、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笙居于前。钧容直为宋军乐队,笙也是其常备乐器。东西班乐是宋皇随驾乐队,乐器有三,小笙为其一:“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觱栗、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对笙这种形似凤、音似凤的乐器,宋人有着特别的偏爱。梅尧臣《答中上人卷》诗云:“吹笛皆学龙,吹笙皆学凤。”他们不厌其烦地把不同形制、种类、功能的笙应用于歌舞表演,宋词演唱在喧天笙歌中有了更多的喜庆意味。笙在歌舞表演上的具体应用,有伴奏、独奏、领奏、协奏、合奏等五种形式。
伴奏。乐器通过与歌舞旋律同步来强化歌舞节奏,可使歌舞表演更加饱满、流畅,是为伴奏。伴奏是笙的基本功能,可单独伴奏,也可与不同乐器一起伴奏,如果是后者则在伴奏中便有了合奏因素。笙簧缭绕,歌舞满眼,清亮的笙声填补了歌、舞、宾客间无形的空白,使宴会弥漫喜庆气氛。李商英《胜胜慢》揭示了笙乐这一气氛黏合剂功能:“笙簧缭绕,画鼓声喧,佳人对舞绣帘前。高卷铺衬,广列华筵,人人献香祝寿,捧流霞,永庆高年。名香爇,睹重重华盖,金兽喷烟。一愿皇恩频降,松柏对龟鹤,彭祖齐肩。二愿子子孙孙,尽贡三元,石崇富贵也休夸,陆地神仙。更三愿,愿年年佳庆,永保团圆。”笙声有着极好的融合性,宋词人每提及“笙”,往往与歌相连,曰“笙歌”,这是对笙伴奏功能的最好阐释。捧笙吹奏的动作与托壶饮酒相近,故宋人谚语又将“吹笙”称为“窃尝”。张元幹《浣溪沙》词序说:“范才元自酿,色香玉如,直与绿萼梅同调,宛然京洛气味也,因名曰‘萼绿春’。且作一首,谚以‘窃尝’为‘吹笙’云。”他在词中描述了这种吹奏动作与饮酒动作的相似与和谐:“萼绿华家萼绿春,山瓶何处下青云。浓香气味已醺人。竹叶传杯惊老眼,松醪题赋倒纶巾。须防银字暖朱唇。”笙歌鼎沸,热闹无比,音色喜庆的笙几乎是节庆筵席上歌唱的必备乐器:“莫把画堂深处负,笙歌引入兰房。满斟玉斝醉何妨。南山堪作誓,福禄应天长。”“称觞设席,香雾腾葱郁。霜天晓,笙歌彻,玉斝倾仙液。”“玉殿阶前排筵会,今宵秋日到神仙。笙歌寥亮呈玉庭,为报圣寿万年。”
笙可以为歌舞喧天、人声鼎沸的热闹场合伴奏,可以为浅斟低唱、优雅低徊的清静场合伴奏,适用于不同风格的歌词演唱。如以写酒宴歌舞著称的张先,其《木兰花》所表现的是低徊百转的笙乐后,歌者与词人的相思:“楼下雪飞楼上宴,歌咽笙簧声韵颤。尊前有个好人人,十二阑干同倚遍。帘重不知金屋晚,信马归来肠欲断。多情无奈苦相思,醉眼开时犹似见。”而其《劝金船·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则是当堂作曲填词演唱,笙箫演奏成为文人雅集的组成部分:“流泉宛转双开窦,带染轻纱皱。何人暗得金船酒,拥罗绮前后。绿定见花影,并照与、艳妆争秀。行尽曲名,休更再歌杨柳。光生飞动摇琼甃,隔障笙箫奏。须知短景欢无足,又还过清昼。翰阁迟归来,传骑恨、留住难久。异日凤凰池上,为谁思旧?”
独奏。单独阐释、演绎一段完整曲义,是为独奏。笙便于携带,坐奏、立奏、移动吹奏均可。中秋时节,丝竹鼎沸,而北宋皇宫笙乐,便是在深夜,对于附近居民来说这宛如天外仙乐,清晰动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宫内参与盛会之人,可以亲身体验这种竽笙凤鸣的美感。万俟咏中秋应制词《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描述了笙部伴奏、《霓裳》曲中唱御词的场面:“宫妆,三千从赭黄,万年世代,一部笙簧。夜宴花漏长,乍莺歌断续,燕舞回翔。玉座频燃绛腊,素娥重按霓裳。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酒宴歌前月下吹笙,从内到外都提高了歌词品味,这一习惯至南宋依旧不衰。宋淳熙九年(年)八月十五日,宋孝宗和太上皇赵构在德寿宫庆中秋,50人的清乐队和近人的教坊乐队在月下“箫韶齐举,缥缈相应,如在霄汉”。赵构犹不尽兴,让小刘贵妃独吹白玉笙《霓裳中序》:“待月初上,箫韶齐举,缥缈相应,如在霄汉。既入座,乐少止。太上召小刘贵妃独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执玉杯,奉两殿酒,并以垒金嵌宝注碗杯盘等赐贵妃。”当时,侍宴官曾觌填有《壶中天慢》词,描述了笙乐、吹笙人与月色歌舞之美:“素飙漾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阕。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
乐器形貌、声音之美对于歌词的影响,这首应制词是一个样本。月下吹笙花影中,和焚香抚琴一样是文人时尚。范成大《醉落魄》写道:“栖乌飞绝,绛河绿雾星明灭,烧香曳簟眠清樾。花久影吹笙,满地淡黄月。”越来越多的乐器乐声进入歌词,强化了歌词韵味,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陈与义“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辛弃疾“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皆是如此。笙之魅力不限于吹奏行为和音乐之美,也体现在听者之优雅。范成大的好友姜夔《虞美人·赋牡丹》就记录了卧看花梢风中摇曳,独听隔帘玉笙吹奏的情景:“西园曾为梅花醉,叶翦春云细。玉笙凉夜隔帘吹,卧看花梢摇动、一枝枝。娉娉袅袅教谁惜,空压纱巾侧。沉香亭北又青苔,唯有当时蝴蝶、自飞来。”吹奏者与聆听者也可以置于同一画面,小童独吹,听者小醉,共处柳风月明中,显示出笙萧散低徊的一面。毛滂《浣溪沙·泛舟》载:“银字笙箫小小童,《梁州》吹过柳桥风。阿谁劝我玉杯空。小醉径须眠锦瑟,夜归不用照纱笼。画船帘卷月明中。”
室内小酌,男女相对,低音笙同样可以用来调节气氛,传达情意。如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需要指出的是,笙独奏之时,吹奏者着彩衣,双手如玉,捧一簇如玉笙管,乐声之外,表演行为本身又是一幅与声乐媲美的图画。如史浩《野庵分题·笋指》对吹奏《阮郎归》笙伎手指的描写:“春来初见着斑衣,一束纤纤玉未肥。试捧银笙按工尺,听君一曲《阮郎归》。”
领奏。在表演中引领乐器或歌者演唱,这是笙的指挥功能,和觱篥“头管”的功能类似。如前引《韩非子》所述:“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领起演奏,协调乐队行为,乃先秦笙作为五音之长的资格。笙的领奏功能在南宋慢词表演中尤为突出。以宋理宗赵昀正月五日天基圣节禁中寿筵排当乐次为例。这个寿宴基本上是一场器乐演奏会,其中领起演奏的乐器有八种,笙和笛乃仅次于觱篥、排名第二的领奏乐器。这八种乐器各自领起次数分别为:觱篥12,笛5,笙5,方响4,嵇琴2,箫1,筝2,琵琶1。笙色祗应人(演职员)参与表演的数量,也远超北宋常用的琵琶色(5人)、杖鼓色(10人)、方响色(6人)、箫色(3人)诸色,仅次于觱篥色(32人)、笛色(48人),为14人:侯璋、叶茂青、任荣祖、董茂、张瑾、潘宝、姚拱、范椿、孙昌、莫正、周珍、马椿、姚舜臣、陈保。
笙和觱篥、笛这些管乐器在表演中的大规模使用,和南宋长调慢词、骚雅风气的盛行同步。考虑到词倚声而填、佐酒侑觞而歌的传统,则舒缓优雅管乐器的大量使用对词风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笙的领奏在整个宴会表演进程中的分布是均衡的,说明这类管乐器和宋词表演的配合已经稳定成熟。寿宴上寿、初坐、再坐三个环节,笙领起演奏曲子五支,其中第一环节三支,后两环节各一支。笙领起五支曲子的位置、曲名、演奏者分别为:上寿环节三支,第三盏,笙起《升平乐慢》,侯璋;第七盏,笙起《恋春光慢》,任荣祖;第十一盏,笙起《庆寿乐慢》,侯璋。初坐环节一支,第九盏,箫起《缕金蝉慢》,傅昌宁;笙起《诧娇莺慢》,任荣祖。再坐环节一支,第三盏,觱篥起《庆箫韶慢》,王荣祖;笙起《月明对花灯慢》,任荣祖。需要指出的是,笙色十四人中,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奏,本次宴会,只有侯璋、任荣祖两人可以。领奏之外,笙同样有独奏曲子两支:初坐一支,第五盏,笙独吹,小石角《长生宝宴乐》,侯璋;再坐一支,第十九盏,笙独吹,正平调《寿长春》。领奏之外,其作为普通乐器的演奏功能不废。
协奏。笙与其他乐器协作演绎一段曲意或一支完整曲子,称协奏。协奏可以是乐器间协作来演绎纯粹的器乐,也可以是多种乐器协作来为歌舞伴奏。宋徽宗赵佶十月十日天宁节生日,十二日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宫中大宴,教坊乐部列于集英殿山楼下彩棚中,当时北宋尚以弦乐器为主,笙在乐器最后一列:“前列拍板,十串一行,次一色画面琵琶五十面,次列箜篌两座……以次高架大鼓二面……后有羯鼓两座……次列铁石方响……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宴会第一盏酒笙与箫、笛的合作,便是协奏的一个样板。歌唱演员表演之后,笙与箫、笛合奏两遍,引领全场的“众乐齐举”,为歌者伴奏,拉开大宴的序幕:“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众乐齐举,独闻歌者之声。”
对于伴奏为第一功能的笙来说,协奏是很正常的事情,乐队中协奏更是如此。这也是词人每提及笙,往往将其与其他乐器并提的一个原因。词人毛幵《江城子·和德初灯夕词次叶石林韵》说“华堂歌舞间笙钟”,笙钟同音,即是京师元夕华堂笙钟协奏伴歌舞:“神仙楼观梵王宫,月当中,望难穷。坐听三通,谯鼓报笼铜。还忆当年京辇旧,车马会,五门东。华堂歌舞间笙钟,夕香濛,度花风。翠袖传杯,争劝紫髯翁。归去不堪春梦断,烟雨晓,乱山重。”李淛《千秋岁·四明赵制置、史开府劝乡老众宾酒》“鼍鼓笙箫沸”则是写鼓、笙、箫三种乐器协奏场面:“鄮峰凝瑞,鄞水浮佳气。晴景转,花光媚。碧幢森大纛,红旆纷千骑。相遇处,满城鹤发群仙萃。绮席张高会,鼍鼓笙箫沸。金兽袅,檀烟翠。玉山环回座,休惜今朝醉。觞再举,清歌共引千秋岁。”
市井散乐,亦多用笙来合乐。如南宋临安,笙是构成细乐、清乐特色的乐器之一。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说:“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也说:“清乐比马后乐,加方响、笙、笛,用小提鼓,其声亦轻细也。”
合奏。合奏是指两支以上的笙合作演奏。笙的合奏有时不是简单的声音叠加,而是大小笙合作演奏,高低声相互应和,形成立体声的效果。先秦即有三笙与一小笙(和)的合奏,《礼仪注疏》云:“三笙一和而成声。”郑玄在句下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尔雅》曰:‘笙小者谓之和。’”宋人邢昺解释《尔雅》中大小笙关系时,也强调这种合奏中有协奏因素:“其大者名巢。巢,高也。言其声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声少,音相和也。”孙炎云:“应和于笙。”朝会等大的场合用笙,多是大小笙合奏,以求音乐的气势恢宏、音质饱满和层次感。毛滂《水调歌头·元会曲》记录了元旦皇帝大会群臣,乐队笙竽合奏的恢弘气势:“九金增宋重,八玉变秦余。千年清浸,洗净河洛出图书。一段升平光景,不但五星循轨,万点共连珠。垂衣本神圣,补衮妙工夫。朝元去,锵环佩,冷云衢。芝房雅奏,仪凤矫首听笙竽。天近黄麾仗晓,春早红鸾扇暖,迟日上金铺。万岁南山色,不老对唐虞。”
三、笙之形制:声乐的丰富物质基础
宋代笙继承了前代传统,材质和种类更多。笙斗以坚木为之,刷漆。笙苗一般为竹管,插入斗中。笙簧、笙嘴用铜。指按音孔,吹吸发声,如龙吟凤鸣。成亻见《乐学轨范》引宋代《大晟乐谱》,略言其通行制作之法:“笙,集竹为之云,用十七管,前八簧,后九簧,高下有次序,竹长者九寸五分,底高二寸五分,共高一尺五寸。”大晟乐十七管笙当是官方标准用笙,成亻见详述其做法:“按造笙、竽、和之制,匏中别用木柱虚其周围,上面以黑角付之,周回凿孔以植管竹,用豆锡造带束之,匏或以木为之,嘴用铜插于匏,口含而吹之,呼吸俱有声;管用乌竹,随律长短,又用刚木穿虚其中,围径与管竹同,长一寸六分,连付管端穿穴于一面,以付簧鍱,管内面各穿长孔,俾通声气,外面又穿圆孔,按之则有声,开之则无声。”
如前文所述,和为小笙,竽为大笙,和、笙、竽的区别一般体现在笙斗口径、笙嘴长度、笙苗长度的不同,上述因素也决定了它们的音质高低之差别。
笙管镶嵌银等金属,以标识音阶高低,称“银字”,又兼有醒目和美观双重用途,故有“银字笙”之称。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说:“银字,制笙以银作字,饰其音节。”徐养原《管色考》说:“镂字于管,钿之以银,谓之银字。”今人李啸仓《释银字儿》有详细描述:“音节本指声调缓急之度。此处言音节,恐怕就是指调节音调之处,如笙笛之之按孔等而讲的。既云‘饰其音节’,当必于笙之按孔处,钿之以银。”常用材质之外,有时也会取其他材质,如金、石,这样的笙有特别的发音效果,也往往成为传世名器。“靖康之变”,宫廷中这类乐器流失在外,“中兴四将”中的张俊(循王)、韩世忠(蕲王)均曾得到过。周密描述时用了“其薄如鹅管,其声清越,真希世之珍也”这样的语词,可见其精美与珍贵。
簧是笙发声的核心部件,铜制。天气冷之时,金属簧片易凝结附着水珠,影响音色与音质,因此保暖是笙乐器冬季维护的大问题,笙之冷暖也随之成为诗词抒情的常用语。周密曾叙述吴郡王(吴益)、平原郡王(韩侂胄)家声伎用笙,可见当日这种乐器生存状态之一斑:“只笙一部,已是二十余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终,日给焙笙炭五十斤,用绵熏笼藉笙于上,复以四和香熏之。盖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靘以绿蜡,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用焙而后可。陆天随(龟蒙)诗云:‘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举此一事,余可想见也。”
宋代雅部、俗部、胡部乐中均有笙的使用,三乐部所用笙有所不同,形成了丰富的种类。兹列举如次:
竽笙。竽笙是宋人对俗乐歌舞表演所用的笙之泛称,通常习用笙,十九簧。“竽笙”这个称呼严格说来并不严谨,竽是大笙,笙是总称,二者合称来指代特定乐器,有些不伦不类。这种不严谨大约也是乐器太流行所致:“近代竽笙十九簧,盖后人象竽倍声因以名之。然竽、笙异器而同和,故《周官》竽与笙均掌之以笙师焉。既谓之竽矣,安得又谓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矣。世人或谓大笙谓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雅部标准笙。太常雅部所用笙,漂亮雅致,外形与结构都秉承周代以来的传统,笙管长四尺,攒排如凤翼,集于匏中,发声似凤鸣,如凤在巢,十九簧者曰“巢笙”,十三簧者曰“和笙”。这应当是标准笙:“盖笙为乐器,其形凤翼,其声凤鸣,其长四尺。大者十九簧谓之巢,以众管在匏,有凤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管谓之和,以大者唱则小者和也。”太常笙,后来经过李照改造,大笙、巢笙、和笙协作,兼有浊、中、清声。
大笙、小笙。笙又有大小之别,其标准在于笙管之多寡。如果笙管数量相同,则以笙管之长短和声音之大小区分:“前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皆用十九数,而以管之长短、声之大小为别。”以太常雅部为例,大笙“声众而高”,为清声,多用于领奏;小笙微而低,为浊声,多用于和声。宋代登歌演奏即是先以大笙领奏,后以和笙烘托整个声部。大小笙其实是相对而言,之所以存在,一则为声音的大小高低配合,一则为声音的清浊轻重配合。陈旸对此有详细辨析:“传曰:‘大笙音声众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不亦笙大小之辨乎?《说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凤身,盖其簧十二以应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闰也。’圣朝登歌用和笙,取其大者倡,则小者和,非阮逸所谓取其声清和也;用十三簧,非阮逸所谓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辨小大之器哉?”
义管笙是通用的笙增加两支可装卸笙管,便于易均变调,如此十七簧笙就具备了十九簧的功能,这应当是熟练乐工的发明。但变宫之际换管太麻烦,宋真宗景德间乐工单仲辛索性将换管后的笙固定下来,不再更换。义管笙遂淘汰不用。
十七管笙、十九管笙、二十三管笙。这是宋朝大乐乐工为便于操作,以及演奏更复杂的乐曲,对胡部笙所作改良的品种。取胡部乐中的十七管笙将其宫管从中间移到左右,来代替之前竽、巢、和诸种笙的功能。更复杂的演奏,可借增加笙簧数量来实现,于是就有了十九管笙和二十三管笙。这种改良,提升了单笙的功能,减少了笙的使用数量,精简了乐队,同时提升了乐器使用效率,的确有利于新兴复杂音乐的表演,符合乐舞新声的发展潮流,却不合“古制”。然而能吸收胡部乐器之长来优化雅乐,说明宋代乐工具有相当开阔的胸襟。
葫芦笙(瓢笙)。杜佑《通典》云:“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于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可知早期笙以匏为斗,唐人以木为斗,而南方边远地区仍存以匏为斗的古风,称为“葫芦笙”。宋至道(—)年间,西南诸蛮曾进贡这种葫芦笙,称“瓢笙”。成熟的瓠一剖为二,即可作瓢,这是瓢笙名称的来历。进贡瓢笙(葫芦笙)的是贵州牱诸蛮,宋人周煇《清波杂志》记录了进贡时表演的情形:“至道元年,西南牱诸蛮贡方物,牱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贡,至是始通。上……因遣令作本国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声,须臾,数十辈连袂宛转,以足顿地为节……皆蓬发黧面,状如猿猱。”
宋人彭汝砺《武阳寨闻峒中作乐》诗写江西民间用葫芦笙:“成康已措刑,文景不言兵。夷俗家家曲,蛮歌处处声。长腰筒拍鼔,细竹葫芦笙。物意惟安乐,人间共一情。”其后诗注对葫芦笙的描述,可以与之印证:“蛮笛长一二尺,孔疏,其声下而清;筒拍鼔长四五尺,以帛系于肩而拍其下;葫芦笙,葫音鹘,以十竹为户,其声不可复辨。”
其时边远地区民族用笙的热情,并不亚于中原,因其材质如匏、竹都是就地取材,反而更便于日常制作使用,久而不衰。湖南辰、沅、靖州一带,日常娱乐聚饮之时,笙更是必用之器:“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
可见,中国古代声乐文化促进了宋词的演唱与发展,这正是宋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突出现象,也是宋代歌舞表演引人注目的亮点,而笙对宋词演唱与创作的影响则是其中若干突出的个案之一。
笙为词人与歌唱提供了一种乐器,更以其深厚的历史意蕴和独特的气质赋予宋词演唱别样的艺术魅力。古老的乐器介入宋朝充满朝气的歌词演唱,风靡四海的歌声中,笙乐再次征服世间之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均为其表现内容,庙堂的黄钟大吕、乡间的村社俚曲皆有其影子。歌咏花间美酒与枕前美人之外,祝寿也是宋词内容的一大宗,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鼎沸的笙歌在场,寿词的表演是不是还会这么热闹。宋词喜庆色彩的发生与维持,乐器笙功不可没。
同样,宋词创作与演唱对于笙的接纳,使得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衰微状态的笙焕发出新的光彩,再次成为歌舞场上的主力乐器。在宋词演唱达到高峰之时,笙也进入了自周朝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嗣后,宋词演唱随宋朝灭亡而衰歇,笙的使用也再次式微,其活动范围再次限于宫廷礼乐和民间地方曲艺,不复有与宋词演唱合作的辉煌。
近代以来,国乐复兴,笙经过了若干改进与发展,如笙斗于圆形之外,又有方形;木斗之外,又有铜斗;运用新技术增加了保温装置;扩充了笙管数量以增加音位,等等。笙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传统乐器,呈现新的时代艺术生命力。但它依旧与当下的宋词演唱一样,是传统声乐文化的遗存与延续,若欲当日那样全民流行,恐怕已不再可能。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年第2期第—页。为方便手机阅读,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jmwc.com/zcmbwh/171946.html